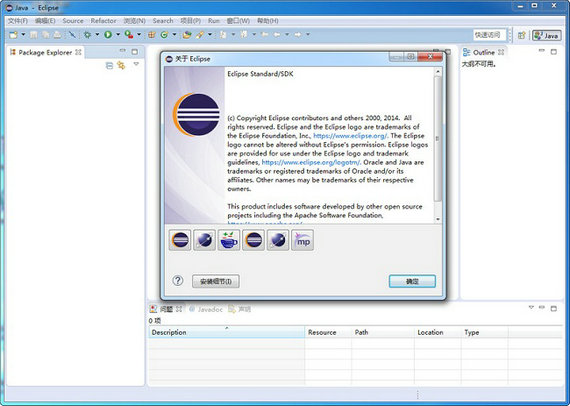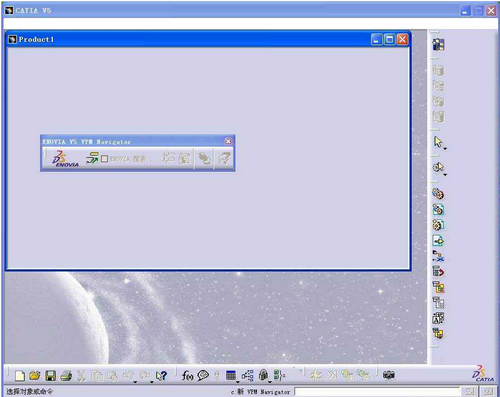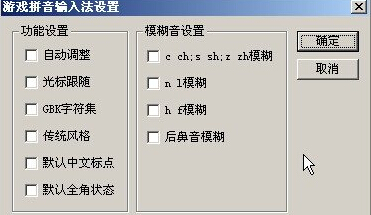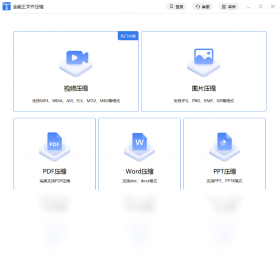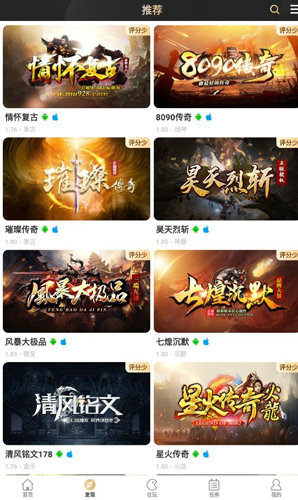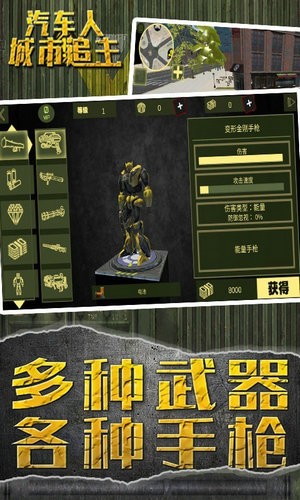刺客信条大革命 官方小说中文翻译
《刺客信条:大革命》小说目前英文版已经发售,而中文版在前代小说汉化完成之前也不会进行汉化,所以为了各位看英文蛋疼的玩家,小编给大家带来来自亚诺多里安吧的“锅贩FG_”翻译,喜欢刺客信条大革命剧情的玩家不要错过。
自亚诺·多里安(Arno Dorian)的日记
1794年9月12日
她的日记躺在我的桌上,翻开到第一页。这是在如潮涌的第一波情绪令我窒息之前我所能阅读的全部,眼前的文字被我眼里的钻石所分解开。泪滑落脸庞,就同关于她的思绪重新闪现:一个顽皮的孩子玩着捉迷藏的游戏;成年的我所渐渐发觉并爱上的纵火者,绺绺穿过她肩上的红色长发,暗且亮泽的睫毛下深邃的眼眸。她有着在专业舞者与剑术大师两者之间的平衡。她就像是在房间里所有男人的贪婪目光下划过殿堂地面的行云流水,与战斗时如出一辙。
但是,藏在那眼后的,是秘密,我即将知晓的秘密。我再次拿起了她的日记,想要将手掌与指尖置于页面,抚摸这些字句,感觉到她独特灵魂的一部分便蕴于其中。
我开始了品读。
自爱丽丝·德·拉塞尔(Elise de la Serre)的日记
1778年4月9日
I
我的名字是塞尔的爱丽丝(Elise de la Serre)。我十岁了。我的父亲是弗朗索瓦(Francois),我的母亲是茱莉(Julie),我们住在凡尔赛宫;华耀,美丽的凡尔赛宫,整洁的建筑和宏伟的城堡(cheateau:中世纪法国城堡)驻扎在这巨大宫殿的阴影中,伴着它的欧椴树大街,它鳞光闪闪的湖水与喷泉,它被悉心呵护的雕塑花园。
我们是贵族。幸运的人。享有特权的人。证据便是我们进入巴黎只需要走过十五英里。那是一条被挂起的油灯照亮的路,因为在凡尔赛宫我们就用这些东西,但是在巴黎穷人用着牛脂蜡烛,而从牛脂工厂里飘起来悬挂在城市上的烟雾就像是裹尸布一般,令肌肤染上污秽,令肺部感到窒息。身着破布,他们的背或是被身体的负担或是被心灵的苦痛所压弯,巴黎的穷人们在街上缓慢穿行并毫无减少的迹象。大街上四处蹿流着裸露的阴沟,泥秽和人类排泄物在其中自由地流动,包裹着那些抬着轿子的人们的脚,就在我们经过时,瞪大眼睛望着窗外时。
不久,我们乘着镀金的马车回到了凡尔赛宫,经过院子里如同鬼魅一般被薄雾覆盖的雕塑。这些赤脚的佃农照料着贵族的领地,同时在收成不好时也在挨饿——土地所有者的实实在在的奴隶。在家我听着父母关于他们怎样整夜保持清醒飒飒地挥动树枝赶走那些鸣叫着的让贵族们保持清醒的青蛙们,还有他们是怎样嚼着草皮活下来的。与此同时,贵族们越来越滋润,免于应付税务,不用服军役,更不必忍受整天在路上苦干却没有薪酬的劳役的屈辱。
我的父母说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Queen Marie Antoinette)在宫殿的走道、舞厅、前厅四处漫游幻想着为自己置办新衣物的方法,而她的丈夫路易十六世国王(King Louis XVI)则懒洋洋地坐在国会议厅(lit de justice)里通过那些富足贵族们的律法,而弃贫穷饥困的百姓于水深火热。他们阴暗地谈论着这些举动可能会怎样地煽动起革命。
II
对于你突然明白某件事的那瞬间有种特别的表述。这就是当“便士掉落”的瞬间(the moment when “the penny drops”)。作为一个尚幼的孩子我从未想过我为什么要学历史,而不是礼教、举止或是体态;我没有质疑过为什么母亲表现得跟父亲一样和晚餐后的“乌鸦们”,她的嗓音逐渐提高尽了像是她所有的气力去争辩;我从没好奇过为什么她不是侧骑在马上,或是为什么她从不需要一名马夫去牵住马匹,还有为什么她从不花大把时间去梳妆打扮或与其他贵妇闲谈八卦。我一次也没有想要去问过为什么我的母亲一点也不想其他的母亲。
一直没有,一直到那枚便士掉落下来。
III
她很美丽,当然,并且常是穿着华丽,虽然她从不在乎优雅服饰的生活方式以及穿旧它们的在天井里撅起嘴非难地高谈阔论着的女人们。从母亲那知道的则是她们为外表和地位所折腰,为物质所折腰。
“她们什么都不会明白当这些打中她们的脑门,爱丽丝。向我保证你永远不会成为像她们一样的人。”
好奇心被激起,想要去知道究竟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于是我利用在母亲裙褶上的有利点偷偷窥视着那帮嫌恶的女人。而我看见的只是流言蜚语的浮夸铺张,假装她们对丈夫的一心一意,而她们的视线实际上却一直在房间内周转打量着她们的仰慕者,寻找着能插进一腿的爱侣。未被看见地,我会瞥向那粉饰的面具的背后,当那轻蔑的笑声干枯在她们的嘴唇上,那讥讽的神态凋零在她们的眼里。我会以她们真实的那一面看待她们,恐惧的她们。恐惧失去这一切好处。恐惧滑下这一社会阶梯。
母亲则不像是那样。至少她把没有什么看的比那些闲谈八卦更轻的了。而且我从没看见她与仰慕者厮混着,她厌恶那些粉末,她更没时间为了炭黑色的美丽的邂逅(beauty spots,一种由金酒、甜苦艾酒、干苦艾酒、橙汁、红石榴糖浆和柠檬调成的微甜的酒)和雪白光滑的皮肤去管任何人,她唯一对于潮流的迁就便士她的鞋。除此之外,她对自己行为举止的关注只是为了一个理由,唯一的理由:保持应有的端庄。
且,她绝对忠实于挚爱的父亲。她站于他身侧,就在身旁,从不在身后——她支持着他,坚定不倚地忠诚着他。我的父亲有许多顾问,克罗切恩·勒夫洛尼亚先生(Messieurs Chretien Lafreniere)、路易斯-米歇尔·路·佩鲁齐先生(Messieurs Louis-Michel Le Peletier)、查尔斯·加百利·西维特先生(Messieurs Charles Gabriel Sivert)和勒维克夫人(Madame Levesque)。穿着他们的黑色长大衣、暗色毛毡帽子和从不露出笑容的眼睛,我叫他们“乌鸦们”,我会经常听见母亲在他们面前维护父亲的立场,支持着他不论如何,虽然她可能会在背后偷偷跟他说些什么。
自从上次已经有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自从上次她与父亲争执。
他们说她今晚可能会死去。
1778年4月10日
I
她顺利度过了那一晚。
我坐在她的床边,握住她的手同她讲话。有那么一会儿我有着似乎是我在抚慰她的错觉,直到她转过头来用她浑浊但是引人深省的眼神注视着我的那一刻,我意识到事实恰好相反。
昨晚我有好几次向窗外下边院子里的亚诺瞅去,十分地嫉妒他能够对仅仅几英尺距离的心痛如此疏忽。他知道她病了,当然,但是消耗性疾病算是很平凡的事,毕竟每天医生都会添几例死亡病例,即使在这,在凡尔赛宫。而且他并不是德赛尔家的人。他是个外来者,从来不是我们最深处、最黑暗的秘密的参与者,这也包括只属于我们的苦痛。甚至,他几乎对德赛尔家的事务一无所知。对亚诺来说,母亲只是一个混迹于城堡上层的遥远模糊的轮廓;在他的认知里,她只是一个纯粹地被她的疾病所定义的人。
不一样的是,我和父亲有着同样的焦虑和暗藏的略视。对外,我们带着伤痛依然照常露脸。我们的哀悼在两年时间的残酷诊疗下逐渐平缓。我们的悲伤是望向我们的众多视线下又一深埋的秘密。
II
我们离便士落地的那个瞬间越来越近。而想到那第一个小插曲,我第一次真的开始对我的父母感到不解,特别是母亲,我把这想作是通向我的终点的路上一根耸立的路标。
· 就是那次在修道院。我第一次进入时只有五岁,幼小的我记忆还是懵懵懂懂的。只是一些印象,真的:一长排一长排列起的床;一段很确切却又有些脱节的记忆——看向挤满烟雾的窗外,树的顶端从雾霭的上缘升起;还有……女院长。
弯下腰,感觉有些不悦,女院长的心狠是出了名的,她会在修道院的走道里荡来荡去,像是在宴会展示一般地用手掌横握着她的手杖。在她的办公室里,它则是被斜放在桌上。而现在我们会谈到它时会说“到你了”,而当时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到我了,当她厌恶我对于快乐的妄想,为我笑点偏低的事实而不快并称我快乐的微笑为傻笑。那支手杖,她说,会将傻笑从我的脸上赶走。
女院长对于那件事是对的。的确。有好一段时间。
之后有一天父亲和母亲来找女院长,是为了什么我则是完全没有头绪,不过在他们的要求下我被叫到了办公室。我的父母从座上转过身来打招呼,女院长站在她的书桌后,脸上不加掩饰的轻蔑显而易见,而对我众多不足的轻率评价只是干枯在了她的嘴唇上。
如果只是母亲一人要见我我想我不会显得如此庄重。我会已经跑向她,并期望我也许会滑向她长裙的裙褶里,滑向另一个世界,跑出这个可怕的地方。但这。是他们两人,而我的父亲就是我的国王。是他定制了我们必须遵从的礼仪缛节;是他最先坚持要将我送到修道院里来。所以我靠近并屈膝行李,等待进一步的发落。
母亲轻轻端起了我的手。我完全不知道她甚至是怎样看见有什么在那的,即使它只是在一旁,而母亲还是瞥见了手掌留下的印记。
“这些是什么?”她质问着女院长,拿起我的手面向她。
我从来没有见过女院长无法保持镇定的时候。但现在我能说她脸色惨白。就在那一瞬,母亲就从作为女院长的客人应有的正式和礼貌成为了播撒潜在愤怒的工具。我们都感觉到了。女院长则感受到得最多的。
她稍有些结巴。“就如我所说的,爱丽丝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并且喜欢搞破坏。”
“于是她被抽打了?”母亲继续质问着,她的愤怒上涨着。
女院长耸了耸她的肩。“不然你想让我如何维持秩序?”
母亲抓起了手杖。“我期待着你有能力去保持秩序。你觉得这个这个让你更有能力?”她将手杖猛然拍向桌子。女院长跳了起来并咽下一口唾沫,她的目光则是直直地盯着我的父亲——一直用着一种奇怪的、深不可测的表情在一旁看着的他,就像是并没有什么需要他插手的的事件发生。“好吧,那么你仅仅只是被误解了,”母亲继续道。“它让你变得更加弱小。”
她站在那,看着女院长,并让她再一次跳了起来,她再次将手杖拍向书桌。接着她牵起了我的手。“跟上我,爱丽丝。”
我们离开了,从那以后我便开始有了家教来教授我的学业。
就在我们奔忙出修道院并在马车里展开一段安静的归途时我知道了一件事。在母亲和父亲为这些未提起的事而气恼时,我认识到所谓的女士们并不像母亲刚才所做的那样表现。至少不是普通的女士们,不论怎样。
另一条证据。那发生在也许大约是一年前,在附近城堡来的一位被宠坏的小姐的生日宴会上。其他与我同龄的女孩们都在玩娃娃,将它们安置好享受下午茶,只是为娃娃们准备的下午茶,而并没有真正的茶叶和蛋糕,而只是小女生们假装喂给它们茶水和糕点——对我来说,即使是当时,看起来很蠢。
不远处男孩们在玩弄着他们的玩具士兵,于是我站在一旁算是要加入他们,而这在一片显然造成了一段震惊的宁静。
照顾我的保姆露丝(Ruth)将我拉开。“你跟娃娃们玩,爱丽丝。”她坚决而又紧张地说,她的眼神在畏缩着其他保姆不认可的目光的同时扎向我。我照着被告诉的做了,弯了腰下去并假装感兴趣地虚构着茶和蛋糕,这些尴尬的插曲过去后,草坪上又恢复了自然平常的状态:男孩玩着玩具士兵,女孩与娃娃,保姆们看管着我们两拨人,而不远处是一群散乱的妈妈们,出身贵族名门的女士们讲着关于锻铁草坪椅的闲言碎语。
我看向那群闲侃的贵妇们,就像母亲一般。我看见了我自己从草坪上的女孩到讲闲话的女士的道路,而我的心头涌动上我意识到的绝对的确定——我不想那样。我不想变成像那些妈妈们一样。我想变得像我自己的妈妈——从闲言碎语的乱麻中抽身而出,能够被看到在远处,一个人,在水边,她独一无二的朴实无华一览无余。
III
我有着来自威瑟洛尔先生(Mr Weatherall,英格兰姓氏,原意“阉羊”)的便笺。以他地道的英语所书写,他告诉我他想见到母亲并要求我在午夜与我在藏书室见面并领着他去到她的房间。他嘱咐我不要告诉父亲。
又是一个需要保守好的秘密。有时我感觉就像是我们在巴黎看见的那些不幸的人中的一员,在被强加的期望的重量下被压弯了腰。
我只有十岁而已。
1778年4月11日
I
午夜时分,我套上长袍,取了支蜡烛摸下了楼来到了藏书室等待威瑟洛尔先生。
他想办法进入了城堡,鬼魅一般地行动,那些狗完全没被打搅,他是如此安静地进入了藏书室而我根本没有听到门被打开及关上。他几阔步穿过空厅,从头上摘下了假发——那被诅咒的东西,他讨厌它——然后擎住了我的肩膀。
“他们说她恶化得很快,”他说,当然是耳语。
“的确。”我告诉他,低下了头。
他闭上眼,而虽然他并不已经苍老——才四十好几,略微年长于父亲和母亲——而岁月已经蚀刻上他的脸庞。
“威瑟洛尔先生和我曾经十分亲近。”母亲曾说过。她说出这番话时会微笑。而我设想她脸红了
II
我第一次见威瑟洛尔先生是在二月份异常寒冷的一天。那个冬天正是一系列酷寒冬季的第一波,但是在巴黎当塞纳河洪涌接而冻住时,那些困顿窘迫的人们在大街上垂死挣扎着,而在凡尔赛情况则是另一番景象。等到我们醒来时早已有人生好了在那些炉格里咆哮的火焰,然后我们会享用热气腾腾的早餐,暖洋洋地裹在绒毛里,在上下午我们四处闲逛时手上也会套上暖和的皮手套。
在那特别的一天艳阳高照,虽然这完全没褪下那彻骨的寒冷。一层薄冰在厚厚的雪地上漂亮地晶光闪闪,它是那么坚硬就连斯格莱奇(Scratch),我们的爱尔兰猎狼犬,也能在上头行走而利爪不至于陷进去。它会试探性地走几步,然后意识到这一好运而兴奋地吠着,接着在我和母亲艰难地试着到达南边草坪边缘的那棵树时它便径直向前冲去。
握着她的手,我一边走着一边从肩上瞥去。远远地我们的城堡在阳光和雪地的反射下熠熠生辉,它的窗户像眼睛一样闪烁眨巴着,然后,我们从阳光下走进了树丛,它便不再那么显眼,就像是被铅笔描摹地一般。我们比平常时要远得多,我发现,再也不在它的荫庇所能及了。
“不要惊慌如果你在树影里看到一位绅士,”母亲说,微微地向我弯下腰。她的声音很安静,我不由得将她的手抓得更紧,她笑了。”我们的在场的并不是巧合。“
那时我是六岁,完全不知道一位女士在那样的一个场合下与一个男人会面会别有“深意”。我所能知道的,仅是单纯地母亲与别人见面,并不比与她和伊曼纽尔(Emanuel),我们的园丁,的谈话有更多重要意义,或是和琴(Jean),我们的马夫,一起溜圈。
冰霜授予了这个世界沉寂。在树林里甚至比覆盖着雪的草地上还要安静,当我们从窄窄的小道上走向树林深处时不自觉地便被感染感到心神宁静。
“威瑟洛尔先生喜欢玩一个游戏,”母亲说,她的嗓音在这一片平和的荣光下逐渐缓和。“他也许会突然出现,一个人必须时刻注意等着他的任何意外。我们应该估计到周围的一切然后逐渐有根据地得出自己的预期。你有看见任何的踪迹吗?”
我们周边的雪地都完好如初。“没有,妈妈。”
“很好。这样我们便能确定附近的只有我们。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最可能躲在哪?”
“一棵树后?”
“好,很好——但是这里怎么样?”她暗示着头顶,于是我伸起我的脖子向上方树冠中的枝叶看去,冰霜在细碎的阳光的下闪烁着。
“观察任何一处地方,始终,”母亲微笑。“用你的眼睛去看,尽最大的可能不要去倾斜自己的头。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的注意力在何处。在生活中你会遇到对手,而这些对手会从线索中尝试着去理解你进而清楚你的意图。让他们不断地去猜测来保持的你的优势。”
“我们的客人会在高高的树上吗,妈妈?”我问道。
她咯咯地笑了。“不。实际上,我早就看见他了。你看见他了吗,爱丽丝?”
我们停顿了一会,我看向面前的那棵树,“没有,妈妈。”
“现身吧,弗莱迪(Freddie),”母亲呼叫着,然后理所当然地,前方几码(一码=三英尺=0.9144米)的地方一名胡子深灰的男人从一棵树后走到我们面前,他从头上摘下三角帽又向我们行了一个十分夸张的鞠躬礼。
凡尔赛的人们有一种特定的方式。他们不管面对谁都会牢牢锁定住自己的鼻子。他们有着我所认为是的“凡尔赛式微笑”,吊在茫然和无趣之间,好像几乎就是在不断地传递着诙谐的打趣话,这就像是,所有在场的人都在接受审判一般。
这个男人并不是凡尔赛的一员;单单从他的胡子就能看出。而且尽管他正在微笑,那不是凡尔赛式的;取而代之,那是柔软同时又庄重的,是一张属于三思而后行而且言出必行的男人的脸。
“你蒙蔽了她的眼睛,弗莱迪,” 母亲说,正值他向前走来,亲吻了母亲伸去的手背,接着对我也做了同样的,再次躬下身来。
“真的吗?”他说,他的嗓音温暖又轰隆作响却毫不造作,一名水手或是士兵的声音。“噢,真该死,我一定失了自己的分寸。”
“我希望还没有,弗莱迪。”母亲笑了。“爱丽丝,来见过威瑟洛尔先生,一名英国人。同时也是我的一位伙伴。弗莱迪,这是爱丽丝。”
一位伙伴?像乌鸦们那样?不,他没有一点与他们相似。与其向我瞪眼,他牵起了我的手,躬下身并亲吻了它。“真令人着迷,小姐(mademoiseller,同英文miss)。”他用略刺耳的声音说。 他的英国腔碾压着这个词“小姐(mademoiseller)”让我无法制止地觉得魅力十足。
母亲以一脸认真的表情正色道。“威瑟洛尔先生是我们的心腹朋友和保护者,爱丽丝。一个你可以随时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去找的人。”
我看着她,感觉有些张惶,“那父亲呢?”
“父亲深深地爱着我们两人,而且十分乐意将生命献给我们,但是像你父亲那样居于要位的男人,需要蔽于家内事责的干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威瑟洛尔先生,爱丽丝——你的父亲不应该被女人所要操心的事所打扰。”她的眼神甚至更加尖利。“你的父亲一定不能被打扰,爱丽丝,你清楚了没有?”
“是,妈妈。”
威瑟洛尔先生点了点头。“我随时在这为你服务,小姐,”他对我说。
我屈膝行礼。“谢谢你,先生。”
斯格莱奇也到来了,兴奋地问候着威瑟洛尔先生,他们俩很明显已经是老朋友了。
“我们能走走吗,朱莉?”保护者问道,他戴上他的三角帽,并向我暗示他们俩要一同走。
我保持在他们身后几步距离,隐约听到些他们低声谈话的短暂片段和不连贯的部分。我听到了“大师”和“国王”,但这只是几个词,我早就习惯的在城堡里门外听见的那一种。在我发现它们所承载的重大意义时这已经是老久以前了。
然后那件事发生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已经记不清事件的顺序。我只记得看见母亲和威瑟洛尔先生在斯格莱奇突然毛发竖起并开始低吼时全都陷入了紧张的气氛。接着母亲迅速转身。我的目光随着她注视的方向而去,并在那看见了它:一只狼矗立在我左方的矮树丛里,一只黑灰相间的狼绝对静止地立在那些树的中间,以十分饥饿的眼神打量着我。
有什么东西从母亲的皮手笼里闪现。一支银制利刃,两快步的功夫她便穿到了我身边,将我揽到她的身后,于是她能在我攥住她的裙角时面对那只狼,伸出她的剑。
在小路的另一边威瑟洛尔先生抓住了准备全力应敌、毛发竖起的斯格莱奇的后颈,而我注意到了他的另一只手伸到了悬在他一侧的剑把。
“等等,”母亲令道。一直手升起挡住了威瑟洛尔先生前方的道路。“我不认为这只狼会攻击我们。”
“我没有那么确定,朱莉,”威瑟洛尔先生警告道。“你傍上的那是一只看上去格外饥饿贪婪的狼。”
那只狼盯着我的母亲。而她同时看向正后方,与我们交谈。“这山丘上没有什么能供它吃的了;是窘迫将它逼上了我们的土地。但我认为这只狼明白如果它攻击我们,它将成为我们的敌人。对它来说在面对无法取缔的力量和他处潜在的食物时撤退会是个再好不过的选择。”
威瑟洛尔先生短短地一笑。“为什么我闻到了寓言故事的难闻气味?”
“因为,弗莱迪,”母亲笑道,“真的有这样一个寓言。”
那只狼继续集中着目光,一点也没有从母亲身上移开,直到最后它垂下了它的头,转身并慢慢小跑了远去。我们看着它在树丛中消失,母亲也收起了剑,站定下来。
我看向威瑟洛尔先生。他的夹克再次被扣上,完全看不出那柄剑的存在。
而且我离那枚掉落的便士又再近了一步。
III
我将威瑟洛尔先生领到了母亲的房间,他要求与她单独见面,并向我保证他能独立离开这里。很好奇,于是我从匙孔中窥视过去,看见了他坐在了她的一旁,牵起她的手并弯下他的头。不一会我便听到了他的抽泣声。
1778年4月12日
I
我向窗外望去,想起上个夏天,在我与亚诺一同玩耍的那些时间,我终于摆脱了种种忧虑再次享受作为一个小女孩的充满喜悦的日子,与他一同跑着穿过宫殿空地上树篱围起的迷宫,为了甜点而拌嘴,却不知忧虑的缓期会是这么短暂。
每天早上我都将指甲深深埋向手掌并问道,“她醒着吗?”而露丝,明白其实我想说的是,“她还活着吗?”,并会再三对我确认母亲安然度过了夜晚。
但这不会很长久了。
II
于是。那枚便士掉落的一刻。它又走近了些。但是首先,又是另一个路标。
在我第一次见威瑟洛尔先生的那年春天卡罗尔一家(The Carrolls)来了。那是一季多么明媚动人的春光。冰雪消融了,底下葱翠的规规整整的绒毯似的草坪便也显现了出来,回到了凡尔赛宫的常态——无瑕疵的完美。被地面上精确修剪的灌木所围绕,我们几乎听不到城里的嘈杂声,而在右侧远处宫殿的斜坡很是显眼,宽旷的石阶通向开阔前厅的石柱。这片光辉华丽为了款待来自英格兰伦敦的梅费尔(Mayfair,伦敦上流社交界与住宅区;同时是加拿大地名)的卡罗尔们也是花了一番功夫的。卡罗尔先生(Mr Carroll)和父亲在客厅里待了好几个小时,显然沉浸于他们的谈话内容中而且乌鸦们时不时也会来插一脚,而母亲和我则是负责款待卡罗尔夫人(Mrs Carroll)和她的女儿梅(May)——她尽力利用每一秒时间来告诉我因为她十岁了而我只有六岁于是她比我要优越多少。
我们邀请她们去散步并穿暖和以防早晨的虽然很快就会被阳光殆尽的清冷:母亲和我、卡罗尔夫人和梅。
母亲和卡罗尔女士在我们前方几步走着。母亲,我则注意到,带上了她的皮手笼,我很好奇那柄利剑是否正被秘密地悬在那。我曾经问过,当然,在那次灰狼的意外发生后。
“妈妈,为什么你要在皮手笼里放一把刀呢?”
“为什么,爱丽丝,当然是为了防止万一遇上四处劫掠的灰狼所带来的威胁。”然后她又添上了一抹别扭的微笑,“既有四条腿的也包括两条腿的。而且,不管怎样,这柄剑帮助皮手笼保持形状。”
但是接着,这很快像是成了习惯,她让我保证让这成为我们的秘密之一。威瑟洛尔先生也是一个秘密。这意味着威瑟洛尔先生教授我剑术,这也成了一个秘密。
不被称为秘密的秘密。
梅和我走在我们母亲的后面的一段恰当的距离。我们的裙边划过草坪,从远处看我们就像在地上滑行而过,完美前行的四位女士。
“你多大了,小不点?”梅飒飒地对我说,即使就像我说的,她已经确立过我们的年龄。两次了。
“别叫我‘小不点’,”我正经道。
“抱歉,小不点,但是再说一次你多大了。”
“我六岁了。”我告诉她。
她给了我一个“六岁是个糟糕的年龄”的咯咯笑,就像她从来没有是六岁一样。“好吧,我十岁了,”她傲慢地说。(还有,除此之外,梅·卡罗尔一直都持着“傲慢”的语气。好吧其实,除非我另外说明,完全可以认为她说的任何话都是傲慢的。)
“我知道你十岁了,”我嘘了她一脸,兴致勃勃地想象着向她伸出我的脚然后看着她平趴在车道的碎石上。
“只是不让你忘记而已,”她说,而我则脑补出当她从地上爬起来的,粘在她痛哭流涕的脸上的碎石。威瑟洛尔先生曾教过我什么来着?块头越大,摔得越惨。
(然而现在我也十岁了我好奇我是否也像她那样自大?当我于更小的或是地位更低的人说话时我有用嘲笑的语气吗?根据威瑟洛尔先生说的,我有些过度自信,我认为说的好听些的“自大”,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和梅像这样互相找不愉快,因为本质上我们十分相似。)
就在我们在草地上转来转去时,前头两位女士说的话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卡罗尔夫人说道,“显然我们对你的教团所要走的方向有些许担忧。”
“你有担忧吗?”母亲说道。
“的确,对于你丈夫的同伴们的意图的担忧。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责任让我们的丈夫做正确的事情。也许,如果你不介意我的说法,你的丈夫在制订方针时略有偏颇。”
“这让在英格兰的我们所担忧。”
母亲咯咯地笑了,“你们当然会担忧,在英格兰的你们死板到从不接受任何的改变。”
卡罗尔夫人止步,“这并不是全部。你对我们国民特征的解读还不够敏锐。但是我略有感觉你是站在哪一边的了,拉塞尔夫人。你自己祈求改变的到来吗?”
“如果这个改变让事情变得更好的话。”
“那么我需要上报你是站在你丈夫的顾问们那一边的吗?我的差事是徒劳的吗?”
“不完全是,夫人。知道我享受来自采取对立激进措施的英国同事们的支持是多么欣慰。但是我无法声称有着与你们相同的最终目的。虽然的确有些许力量在推动对权力的暴力颠覆,同时的确我的丈夫相信于上帝指认的君王——确实他的理想道路上不存在丝毫的改变——我自己则涉足了那条中间线。第三条道路,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许当你知道我将我的观念看作三者的中和时并不会惊讶。”
他们继续走了几步,而卡罗尔夫人点了点头,思考着。
母亲打断了沉默,“我很抱歉如果你不觉得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卡罗尔夫人。如果这让我像是个靠不住的女闺蜜我向你表示歉意。“
另一位女士点点头。“我明白了。好吧,如果我是你,拉塞尔夫人,我会运用我两面的影响力来落实你的中间线。”
“对于那个问题,我并不想说,但是请放心你的旅程并不是无用的。我对你和你们的教团分支的尊重如同我所期望换得的同样坚定。你可以在两件事上信赖我:首先,我会绝对遵守我自己的原则;还有,也是第二,我绝不会允许我的丈夫被他的顾问们所动摇。”
“那么你已经给了我我所想要的。”
“非常好。这是或多或少的安慰吧,我希望。”
在后方,梅将她的脑袋靠向了我。“你的父母有告诉你关于你的命运吗?”
“没有。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命运’?”
她把一只手挡在嘴边,装作好像已经说了太多。“他们会的,也许,当你到了十岁时。就像他们对我那样。你多大了,顺便问下?”
我叹了口气。“我六岁了。”
“好吧,或许他们会在你十岁的时候告诉你,像他们对我那样。”
结果,当然,我的父母是被逼无奈的,他们不得不早上许多地告诉了我我的“命运”,因为在两年后,在1775年的秋天,当我刚满八岁时,母亲和我出门逛街买鞋。
III
跟在凡尔赛的城堡一样,我们在市区也有一幢相当大的宅子,而无论何时只要我们在那时,母亲总是想去逛街。
如同我说过的,就算她对绝大多数潮流十分轻蔑,厌恶仰慕者们和假发,在她的长袍上也只压住最基本的华丽的底线,然而在有一件东西上她是十分难以满足的。
鞋。她非常爱鞋。她从巴黎的“基督徒”(店名)那买绸缎制的鞋,比时钟发条还要准时,总是两星期一次,因为那是她的一项不多得的奢侈,她说,同时也是我的,毕竟我们总是带着一双她的以及我的鞋离开那。
基督徒在污浊的巴黎的绿色地段之一,离我们在圣路易斯岛(Île Saint-Louis)上的别墅非常远。但是依旧,一切事情都是相对的,我发现自己在被侍从帮着从舒适而芳香的马车里出来到吵闹、拥挤的街上时屏住了呼吸,这些声音有人们的叫喊,和马蹄的碰撞,还有持续不断的马车轮的辘辘声。这是属于巴黎的声音。
在我们上方女人们交叉着手臂靠在窗户上看着世事变迁。贩卖水果和布匹的货摊在街上排成一行,叫喊的男人们和穿着围裙的女人们推着堆着高高的货物的推车马上向我们喊道。“夫人(Madame)!小姐(Mademoiselle)!”
我的眼球被拉到了街角的阴暗处,看见阴影底下苍白的面孔,我能脑补到当那些眼神非难而饥渴地看着我们时,我在那些眼睛里看见的是挨饿和绝望。
“快跟上,爱丽丝,”母亲说,于是我像她那样提起我的裙子挑剔地踏过脚下的泥土和排泄物,随后我们便被店主引入了基督徒。
相关下载
相关文章
更多+热门搜索
手游排行榜
- 最新排行
- 最热排行
- 评分最高
-
休闲益智 大小:35 MB
-
主机游戏 大小:50M
-
赛车竞速 大小:70.22mb
-
飞行射击 大小:67.74MB
-
动作塔防 大小:54MB